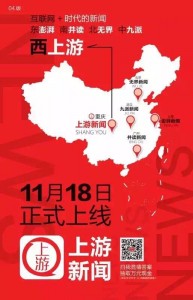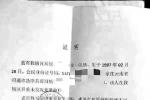从叫兽、妓者到公知——传统精英职业在中国的下流化
昔日那些带着神圣光环的精神职业群体,都面临着巨大的形象危机,形象下流化四大原因:一,现代化祛魅,世俗化让传统赋予这些职业的神圣光环被无情剥离;二,消费社会使顾客成为上帝;三,期待太高,相对堕落感最强烈;四,网络使权力资本发生转移,大众成功实现对精英的逆袭。
对当下中国舆情很敏锐的人,可以清晰地洞察到一个现象,昔日那些带着神圣光环的职业群体,都面临着巨大的形象危机,都被拖进了一个受到大众排斥和仇恨的舆论漩涡中。过去添加于其身上的神圣性已经被暴戾的大众击得粉碎,一个职业昔日越是被神圣化,今日越是被污名化和妖魔化。
这绝不是想像出来的伪问题,我说出这些名字,你就会认同我的判断:医生、教师、知识分子、记者。
一
医生是最典型的。身为一个医生,在过去的社会,这个身份是多么令人尊敬,这个职业是多么的体面。“白衣天使”是人们赋予这个职业的美誉,它背负着很多神圣的使命,这些使命使医生披着很多光环,并使他们成为社会的中上层。可是,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从最新发生在浙江温岭的杀医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风波,可以看到医生的生存状态已经到了一种如何恶劣的地步。被社会仇恨,戴着头盔防医闹,医院需要警察入驻才能防范医生被殴打,被舆论骂成“白眼狼”。神圣性已经荡然无存,而只剩下了敌意和屈辱。
然后是教师。医生是天使,教育是园丁,这是我们儿时常用的比喻,“园丁”的比喻就是一个神圣的光环,但如今这些比喻都已经成了嘲讽。不断曝光的丑闻,从性侵女童到体罚孩子,从惟利是图和贪得无厌的收礼,到层出不穷的师德败坏新闻,已经使老师和校长成为贬义词。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曾经是最和谐的关系之一,可如今也充满了强烈的敌意与对抗。
再就是知识分子。这个就更明显了,从“专家”被称“砖家”,“教授”成为“叫兽”,知识分子被称为“公知”,可以看得出舆论对这个群体的不满。知识分子和医生一样,身上也曾被赋予无数光环,传道授业解惑的期待,社会良心的期许,“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见证着这个职业的神圣性。可那都已经是过去,如今的舆论场中人们以骂专家为流行,以嘲讽教授为乐事,以“公知”作为骂人的标签,除了文革,知识阶层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如此狼狈。
最后是记者。记者也是一个被赋予了很多光环的职业,人们称之为“代言者”,喻之为“了望者”,尊之为“第四权力”,记者也自自诩为无冕之王。可这个记者节,记者们感受到了这种尊重吗?没有,记者已成“妓者”,媒体已成“霉体”,防火防盗防记者,不仅是一些官方的态度,民间也对这个群体流露出这种敌意。假新闻,有偿新闻,有偿不新闻,将那些神圣的光环击得粉碎。
二
是什么使这些过去被神圣化的职业反被污名化呢?为什么越神圣化的职业,在今天反而越遭遇着被妖魔化的危机?
是现代化发展所导致的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这样描述过现代化的场景: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伯曼后来借用马克思这段话所写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表达了同样的忧伤。职业身份在现代化中也经历了一个无可奈何的祛魅过程,传统的时代给医生、老师、记者、知识分子之类的职业赋予了太多神圣意义,而现代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这个世俗化的过程会无情地撕去添加在这些职业上的神圣光环,而回归一个普通的职业。
尤其是在市场化的进程中,这些曾受到尊崇的职业都已经成为“服务业”。上帝已死,教师不是上帝,医生不是上帝,知识分子不是上帝,客户才是上帝!人们不再以充满敬意的目光看待这些从业者,而是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消费者角度来看待这些提供“服务”的人:医生提供的服务能不能让患者满意,教师提供的服务能不能让学生满意,记者提供的信息服务能不能让读者满意?当神圣的崇敬被抽离而只剩下服务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时,会产生一种报复性的反弹,具体表现就是那些职业在舆论中的污名化。
三
是这些群体的道德滑坡导致社会不满吗?可能也有,因为这些职业被赋予了很多神圣职责,一旦这些行业曝出一些丑闻,人们会更加无法容忍。商人生产有毒食品,人们虽会感慨世风日下,但不至于捶胸顿足,因为人们对商人的道德本就没有过高的期待。但如果医生、教师、知识分子出了问题,哪怕只是极端个案,哪怕只是一句冷漠的话,人们都无法容忍。因为在那些神圣的光环下,人们对这些职业有较高的道德期待。
这个时代的道德生态确实出了问题,互相伤害互相投毒,城市给农村生产假药假酒,农村给城市提供农药蔬菜催熟西瓜,做馒头的不吃自己做的馒头,建房子的不住自己建的房子,相比之下,客观来看,医生、教师、记者、知识分子还算是道德水平较高的群体,这些行业还有着较稳固的职业精神,失德是个别的,但因为人们对他们期待过高,这些职业给人的“相对堕落感”可能是最强烈的。
四
这些职业遭遇无情的污名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权力转移。
医生、教师、记者、知识分子之类的群体之所以能在传统时代获得那么尊崇的地位,源其他们掌握着权力资源。医生掌握着对患者治疗的权力,教师垄断着传道的权力,记者手中握有话语权,知识分子则享受着文化阐释权和价值生产权。这几种职业掌控着大众从身体、文化再到精神世界的生活,那些神圣的意义,就是在这种“我主宰—你崇拜”的支配性权力中所生产出来的。
而互联网改变了一切,互联网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技术革命,而是社会深处的革命,使权力发生了颠覆性的转移。大众从互联网上获得了一种翻身做主人的民主力量,他们利用多数人的身份所形成的民粹力量成功地实现了权力的逆袭,将昔日那些戴着神圣光环的职业群体踩到了自己的脚下。这是一场自生自发的网络文化大革命,每个网友可能都是革命红小将。
浏览中国的微博就可以发现,期间充斥着反智反精英的狂欢情绪。这是一种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互相强化和激发,当现实社会越是崇拜权力,游戏规则完全受强者和精英支配,贫富差距阶层撕裂,虚拟空间便越会呈现出反智、反精英、反权贵的特性。人们在现实中受到的挫折,会选择在虚拟的空间中赢得精神补偿,获得一种虚幻的愉悦感。与之对应的一个现实是,现实中如鱼得水的人物,那些被大众看成是强者、既得利益者的人,在互联网上往往会被拍得体无完肤;而在现实中并不如意的弱势者,在网络上往往能获得一种道义上的优越感,并常常在各种虚幻的网络讨伐中大获全胜。
医生、教师、记者、知识分子们的遭遇就是如此,这些群体虽然拥有权力,但在互联网上人数并不占优,相反,他们相对应的另一方倒是人数占优,患者、学生、读者、受众等等。在实际的权力关系上,医生相对患者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教师对学生、记者对受众、知识阶层对大众也同样如此。在互联网上获得麦克风和话语权的大众,带着“弱者”和“受害者”的情绪,将他们想象中的、对象化的强者当成了敌人,进行着一次又一次自以为“正义”的讨伐。